安德烈·莫洛亚 (沈怀洁 译)
“‘钢铁’①什么价钱?”约翰·莫尼埃问道。
“五十九又四分之一,”十二个打字员中的一个回答说。
打字机嗒嗒的声音好象爵士音乐的节奏一样。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曼哈顿岛上的摩天大楼。电话铃不断地响着,打字机的滚筒以惊人的速度卷出无数带有字母的数字和纸片,这些纸片充满了整个办公室。
“‘钢铁’什么价钱?”约翰·莫尼埃又问道。
“五十九,”裘脱路特·密勒回答。

她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向这位年轻的法国人看了一眼。他垂头丧气地瘫在一张椅子里,两手棒着脑袋,看样子非常懊丧。
“又一个玩输了的家伙,”她心想,“真是活该……芳尼也是活该……”
约翰·莫尼埃是霍尔曼银行纽约办事处的随员,两年前和他的美国女秘书结了婚。
“‘开纳各脱’①多少钱?”约翰·莫尼埃又问。
“二十八,”裘脱路特回答说。
门后有人叫换。哈里·可勃进来了。约翰·莫尼埃站了起来。
“好热闹,”哈里·可勃说,“整个股票价格表上的时价都跌了百分之二十!到现在还有些傻瓜说这不是危机呢!”
“这的确是危机,”约翰·莫尼埃说,说完就出去了。
“这一位一定是亏了本啦,”哈里·可勃说。
“是呀!”裘脱路特·密勒说,“他这是孤注一掷。芳尼告诉我的。今晚她就要离开他了。”
“有什么办法呢?”哈里·可勃说。“是危机临头呀!”
电梯的美丽的铜门开了。
“下楼,”约翰·莫尼埃说。
“‘钢铁’多少钱?”开电梯的问道。
“五十九,”约翰·莫尼埃说。
他是一百十二块买进。现在每股亏本五十三块。买进的其他股票也好不了多少。在亚利桑那州的时候赚下的一笔小小的财产,全都做了股票生意。而芳尼是从来没有一个子儿的。这下子全完了。当他到了街上,急步向地铁车站走去时,他就考虑起今后该怎么办的问题来了。重新再来?假如芳尼能鼓起勇气的话,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回忆起从前那段奋斗的经历,沙漠中看守的畜群,接着很快地发达起来的事业。他现在才不过三十岁。然而,他知道芳尼是冷酷无情的。
她的确是这样。
第二天早晨,约翰·莫尼埃独自醒来的时候,觉得自己一点勇气也没有了。虽则芳尼那么冷酷无情,他终究是爱过她的。黑人女仆给他端来了一片甜瓜和稀粥,接着就问他要钱。
“太太在哪里,先生?”
“旅行去了。”
他给了她十五块钱,然后自己算起账来。他还剩下六百块不到一点。这点钱只够他过两个月,也许三个月……以后怎么办呢?他从窗口望下去。这一个星期以来,报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关于自杀的新闻。银行家,经纪人,投机商——这些人都宁愿死而不想再继续那场已经失败了的奋斗。从二十层楼上跳下去吗?要几秒钟?三秒?四秒?然后是粉身碎骨……可是,假如没摔死呢?他想象着那种剧烈的痛苦,四肢摔断了,血肉模糊。他叹了口气,腋下夹着一张报纸,到饭馆吃午饭去了。他自己也觉得惊讶,今天吃果酱抹饼味道反而特别好。
“‘新墨西哥,坦纳托斯大旅社……’谁寄来的这封信,地址又这样奇怪?”
另外还有哈里·可勃的一封信,他就先看了这一封。老板的信上问他为什么没再到办公室去。他的债务是八百九十三元……问他在这个问题上打算怎么办?……多么残酷的问题,或者可以说是幼稚的问题。但是哈里·可勃可没有幼稚这个缺点。
另一封信上面印有三棵柏树①,下款是坦纳托斯大旅社。
经理:亨利·包斯脱歇。
亲爱的莫尼埃先生:

今天我们给您写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关于您的消息,心想也许我们可以为您效劳。
您一定也曾经注意到,即使是一个最勇敢的人,他的一生中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十分不利的情况,这时候,再继续奋斗下去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产生了死的念头。好象死可以解脱一切痛苦。
两眼一闭睡下去,不再醒来,不再听到别人的质问和谴责……我们中间很多人曾经这样想过,并且也下过这样的决心……可是除了少数几个例子外,很多人都不敢解脱他们的痛苦,您只要看看那些曾经试行自杀的人就知道了。因为大多数自杀的情况都是很失败的。有人想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结果只是打断了眼神经而变成了瞎子。也有人服了些药物,自以为会就这样睡去、中毒死掉,谁知却弄错了药的份量,三天后又醒了过来,结果脑子坏了,记忆力受了损伤,四肢也瘫痪了。自杀是一种艺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办到,逢场作戏是不行的,并且由于它的性质关系,也不可能积累经验。
亲爱的莫尼埃先生,假如这问题如同我们所料想的那样使您感到兴趣,我们可以供给您这种经验。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上,我们有一个旅馆,因为那一地区偏僻荒芜,我们可以不受任何管束。我们的任务就是给那些由于某些严肃的、不可避免的原因而希望结束自己生命的弟兄们贡献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能使您达到目的而毫无痛苦,我们甚至敢于说: 也毫无危险。
在坦纳托斯大旅社里,死亡将在您的睡梦中来临,来得十分温和。十五年来我们不断获得成功,在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技巧(去年我们接待了两千多位顾客),就是以极少的药量,顷刻之间收到成效。还有,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对这样的事总有所顾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有一种很聪明的办法来除去您良心上的负担(假如您赏光到我们这里来,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知道大多数顾客没有多少钱,因为自杀的可能性是和拥有钞票的多寡成反比例的。因此我们尽可能把价钱降到最低的限度,而服务质量则毫不减低。您来以后只须付三百元钱。这笔数目包括您在我们这里的一切费用(究竟将待多长时间,您自己是无从知道的),以及手续费,埋葬费,坟墓管理费。由于某些明显的理由,一切服务费用都包括在内,不再向您索取任何小账。
还要向您介绍的是坦纳托斯周围的自然风景十分美丽,那里还有四个网球场,一个十八孔的高尔夫球场和一个游泳池。这里的顾客中有男客也有女客,而且差不多纯粹是上层阶级,因此这里环境的幽雅,尤其是地方的奇特,更是无可比拟。旅客们只须在地敏车站下车,旅社的汽车就会来迎接。旅客们如果准备来,须在至少两天前用信或电报通知我们。电报地址:新墨西哥·考罗纳多·坦纳托斯。
约翰·莫尼埃玩了一盘纸牌,卜算事情是否能成功;这办法还是芳尼教给他的。
在漫长的旅途中,火车驰过一片片的棉田,棉田泛起层层的白色浪花,黑人们在地里干活。两天两夜在打打瞌睡、看看书中间过去了。之后窗外景物更加巍峨雄壮,也更加幽美了。列车奔驰在山溪之间,两旁耸起极高的岩石。紫色、黄色、红色的光带在山上纵横交错地闪烁着。半山腰上飘着一溜长长的云彩。当火车先后停靠在一些小站时,可以隐约望见头戴宽边毡帽、身穿刻花皮上衣的墨西哥人。
“下一站就是地敏车站,”卧铺车厢的黑人对约翰·莫尼埃说。“要擦皮鞋吗,先生?”
那法国人整理了书,把箱子关好。这最后一次旅行竟如此简单,使他很觉惊奇。他听到瀑布的声音。车轮轧轧地响着,火车停住了。
“到坦纳托斯去吗,先生?”一个印第安搬运夫沿着车厢奔过来问。
这人的小车上已经放着两个年轻金发姑娘的行李,那两个姑娘跟在他后面走着。
约翰·莫尼埃心想“难道这两位美貌的姑娘是到这儿来寻死的吗?”
她们也严肃地朝他望着,还低声地说了些什么,但他没能听见。
坦纳托斯的车子,并不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象一辆灵车。车身是天蓝色的,里面的座位是蓝色和橙色的。它在阳光底下,在广场里其他破旧车辆中间闪闪发光;破旧车辆使这个广场看起来活象一个破铜烂铁的市场,还有些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在广场上咒骂着。路旁石块上长满了藓苔,给那些石块罩上了一件蓝灰色外衣。再高一点的地方,五光十色的金属矿石发射着光芒。司机是一个眼睛突出的胖子,穿着一身灰制服。约翰·莫尼埃就坐在他的旁边,一方面是为了谨慎,另一方面也为了好让他的两位女伴独自坐在后面。车子沿着象发夹一样弯弯曲曲的山路,直向山上冲去;这时候,那法国人就和司机攀谈起来:
“你当坦纳托斯的司机已经很久了吧?”
“三年了,”那人自言自语似地说。
“倒是个古怪的职务。”
“古怪?”另一个回答说。“为什么说古怪?我开我的车,这有什么古怪的?”
“你送上去的旅客有没有再下来的?”
“这种情况不常有,”这人有些为难似地说。“这种情况不常有……但是也曾经有过,我就是其中之一。”
“你?真的?……你也曾经作为一个……顾客来到这里?”
“先生,”司机说,“我接受了这个职务,答应不再谈起我的事情,而这里的弯路又是这么难走。您想必不愿意我把您和这两位小姐摔死吧!”
“当然不罗,”约翰·莫尼埃说。
他觉得自己这回答很滑稽。便微微地一笑。
两个小时以后,司机一声不响地用手指头指了一下那边高地上的坦纳托斯大旅社的侧面。
旅社的建筑是西班牙一印第安式的,房屋很矮,房顶上有平台,墙是红色的,上面的水泥是模仿陶土花纹的粗线条。房间的窗是朝南的,窗外便是阳光照耀下的长廊。一个意大利守门人来迎接旅客们。这一张刮得光光的脸立刻使约翰·莫尼埃想起了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大城市里的街巷和路旁鲜花盛开的大马路。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吧,”他问那守门人,这时候,一个仆人接过了他的箱子。
“在巴塞罗那①的里兹旅社,先生……我的名字叫萨各尼……我是在革命爆发的时候离开那里的……”
“从巴塞罗那到新墨西哥! 多长的旅程呀!”
哦,先生,看门人的职务在哪儿都一样……只是,这儿要请您填的表格可比别的地方要复杂一些……先生想必会原谅我的……”
交给这三位客人的印好的表格上确实有很多的格子、问题和备注。必须非常准确地填写出生年月和住址,以及发生意外时应通知的人的姓名地址。
“请至少写下两个亲戚或朋友的地址,并用您自己常用的字体,照下列格式A,手抄一份:
“我名叫×××,身体和精神完全健康,我保证我是自愿抛弃生命,如发生意外,坦纳托斯旅社主管方面及其他人员并无任何责任……”
那两位漂亮的姑娘面对面坐在他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她们很仔细地在抄写A项。约翰·莫尼埃看到她们选用的是一份德文的表格。
旅社经理亨利·包斯脱歇是一个沉静的人,戴着一副金丝眼睛,他对自己这份企业十分自豪。
“这旅社是您的吗?”约翰·莫尼埃问他。
“不,先生,这旅社属于一个股份公司,不过这是我发起的,并且我是这里的常务经理。”
“你们这里的政府当局倒不找你们什么麻烦?”
“麻烦?”包斯脱歇先生十分惊讶地说。“我们除了履行我们做旅店主人的职务以外,什么也没做呀,先生。我们供给顾客们所想要的东西,他们所希望的一切东西,除此以外,什么也没做……再说,先生,这里并没有政府。这块地方的分界线划得很不明确,谁也不知道这里究竟属于墨西哥呢,还是属于美国。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这块高地是无法居留的。传说几百年前有一群印第安人曾聚集在此地,他们是为了逃避欧洲人的追逐,到这里来死在一起的; 当地的人说,就是这些死者的灵魂禁止人们到这座山上来。所以我们能用非常便宜的价钱买下这片土地,在这里过一种独立的生活。”
“顾客的家属从来也不向你们追究吗?”
“向我们追究?”包斯脱歇激愤地叫起来了。“为什么,我的天?到哪个法庭去控告我们?顾客们的家属是十分高兴的,先生,因为他们看到,象这样一些细致的、通常总是很令人难堪的问题,能毫不声张地结束掉……不,不,先生,这里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很漂亮,很正常,顾客就是我们的朋友……您要不要看看您的房间?……假如您同意,就请住113号房间……您不迷信吧?”
“一点也不,”约翰·莫尼埃说。“不过,我是从小就信教的,想到这是自杀,就有些不痛快……”
“可是这并不是、也不会是什么自杀不自杀的问题,先生!”包斯脱歇说这话的声调是如此坚定和不容置辩,使对方没话可说了。“萨各尼,你一会儿领莫尼埃先生看一下113号房间。至于那三百元钱,先生,请您顺便到会计那里去付一下,会计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的隔壁。”
在夕阳斜照的113号房间里,约翰·莫尼埃先生想寻找致死的凶器,但一点痕迹也找不到。
“什么时候开晚饭?”
“八点三十分,先生,”仆人说。
“要不要穿礼服?”
“大部分绅士们都穿的,先生。”
“好吧,我也换一下……给我准备一条黑领带和一件白衬衫。”
进了大厅,他当真看到妇女们都穿着袒胸的晚礼服,男子们在抽烟。包斯脱歇殷勤谦恭地迎面而来。
“啊!莫尼埃先生……我正找您呢……您没有伴儿,我想也许您会高兴和我们的一位女客可贝·萧太太同桌吃饭吧。”
莫尼埃有些为难地说:
“我不是到这里来过风雅生活的啊……不过……您能不能暂时别介绍,先把她指给我看看?”
“当然可以,莫尼埃先生……穿白色绉缎长裙的那位年轻妇女就是可贝·萧太太,现在正坐在钢琴旁边,翻着一本杂志……我想她的外貌不惹人讨厌吧……决不会这样……这位夫人十分随和,举止文雅,又聪明,又是个艺术家……”
可贝·萧太太确是一位很漂亮的女人。棕色的头发,梳成小发鬈,低低地扎成一束,直拖到颈后,托出一个高高的、庄严的前额。两眼又柔和又机灵。为什么一个这样惹人喜爱的人却要寻死呢?
“可贝·萧太太是不是……这位夫人是不是抱着和我同样目的而到这里来的?”
“当然罗,”包斯脱歇先生说,他好象十分着重地说出这个副词来:“当—然—罗。”
“那么,请给我们介绍吧。”
这一顿简单、美味而服务又周到的晚餐结束的时候,约翰·莫尼埃已经知道,至少是概略地知道了克拉拉·可贝·萧的身世。她曾经嫁给一个很有钱,心肠也很好的人,可是她从来也没爱过他。后来她在纽约遇见了一个诱人的、无耻的青年作家,六个月前,她离开她的丈夫,跟随这作家到欧洲去了。她满以为一等她离婚的事办好后,这年轻人就会同她结婚,不料一到英国,他就想尽快地摆脱她。看到他竟这样冷酷无情,她又惊讶,又伤心。她想使他明白,她为了他已经抛弃了一切,而现在又是在这样可怕的处境中,可是他却哈哈大笑,对她说:
“真的,克拉拉,你简直是另一个时代的人……假如我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位女英雄,我早就把你留在你的丈夫和孩子们身边了……你应该再回到他们那里去呀。亲爱的!……你生来就是为了乖乖地照顾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的。”
这时候,她还有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去求她的丈夫诺门·可贝·萧再让她回去。假如她能单独和他会面,她一定很容易使他回心转意的。可是他周围的亲友不断对他施加压力,这对克拉拉十分不利。诺门始终没有宽恕她。经过了多次屈辱的尝试,结果还是没有成功。有一天早晨,她发现她的信件中有坦纳托斯的广告,于是她明白,这才是她唯一解决痛苦的办法,这个办法既干脆,又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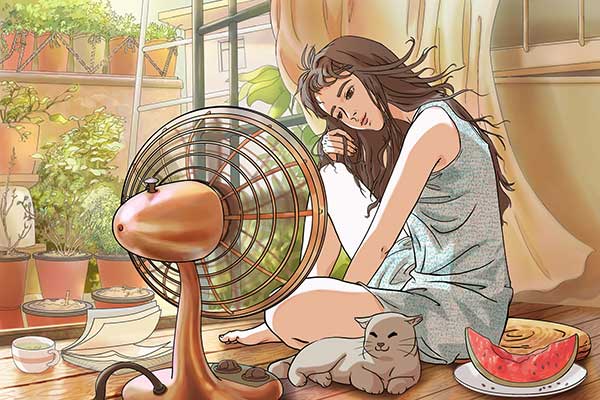
“您不怕死吗?”约翰·莫尼埃问她。
“是啊,当然怕的罗……但我更怕活着……”
“这个回答很漂亮,”约翰·莫尼埃说。
“我并不是想说得漂亮才这样回答的,”克拉拉说。“现在,您说说您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吧。”
听完了约翰·莫尼埃的叙述之后,她十分责怪他。
“这真是难以叫人相信!”她说,“怎么?……您为了您的股票跌价就想寻死?……您难道不知道,假如您有勇气活下去的话,一年,两年,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后,您会忘了这些,也许您所损失的还会赚回来?……”
“我的损失也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说真的,如果我还有其他理由活下去的话,这点事情也算不了什么……我刚才不是也告诉过您,我的妻子离开了我……在法国、我既没有近亲,又没有好友……何况,坦率地说吧,我在感情上遭受欺骗之后离开了我的国家,现在我还能为谁而奋斗呢?”
“为了您自己……为了那些将来会爱您的人……这些人您将来会遇上的……不要因为在自己的痛苦经历中看到某些女人的不良行为,就对其他女人也不公平地一概抹杀……”
“您真以为有这样的女人吗?……我意思是说我可能爱的女人,并且她们还肯跟我过几年贫困、艰难的生活……?”
“我可以肯定说有这样的人,”她说,“有些女人是喜欢艰苦生活的,她们在贫困中会找到一种罗曼蒂克的吸引力……譬如我,就是这样。”
“您?”他恳切地问道。
“噢,我的意思只是说……”
她停住了,犹豫了一下,又接下去说:
“我想咱们该回到大厅里去了,餐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旅社老板已经无可奈何地在我们周围踱来踱去了。”
“您觉得,”他说,一面替克拉拉·可贝·萧披上黄鼬皮外衣,“您觉得……今晚不会……?”
“噢,不会的!”她说,“您刚刚来到……”
“那么您呢?”
“我来了两天了。”
他们分手的时候,约好第二天早晨一起到山上散步去。
早晨,日光斜映在走廊上,照得又明亮又暖和。约翰·莫尼埃洗了一个冷水淋浴。他自己想想也觉得奇怪:“活着多好啊!……”后来他又想到他身上只有几块钱了,也只有几天好活了。他叹了口气说:
“十点了!……克拉拉该要等我了。”
他赶紧穿好衣服,穿的是一套白麻布的衣服,自己觉得很轻松。在网球场上,他见到了克拉拉·可贝·萧,她和他一样,也穿了一件白衣服,这时正和两个矮小的奥国姑娘在一起散步;那两个姑娘一看到这位法国人就溜走了。
“她们怕我?”
“她们见了您有些羞怯……她们正在给我讲她们的身世呢。”
“有意思吗?……您一会儿讲给我听听……您昨晚睡得好吗?”
“睡得很好。我疑心好事的包斯脱歇在我们的饮料里掺了一些安眠药。”
“我想不会的,”他说,“我睡得象块木头一样,可是睡得很自然,今天早上觉得十分清醒。”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而且十分愉快。”
她微笑着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回答。
“走这条小路吧,”他说,“把那两个小奥国女人的事讲给我听听…您就做我的山鲁佐德①吧。”
“但我们的夜不会是一千零一夜……”
“啊,……‘我们的’夜……?”
她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这两个姑娘是孪生姊妹。她们是在一起长大的。起先住在维也纳,后来就住在布达佩斯。她们没有什么知已朋友。十八岁那年,她们遇上了一个匈牙利人,他出身在一个贵族家庭,长得象天神一般漂亮,音乐才能又能与吉卜赛人相比。姊妹俩在同一天发狂似地爱上了他。几个月以后,他向两姊妹中的一个求婚了。另一个在绝望之下试图投河自尽,但没有成功。于是被选中的那个也决定拒绝尼盖伯爵的求婚,两姊妹还打算一起自尽……就在这时候,象你我的情况一样,她们接到了坦纳托斯的广告信。”
“多么痴情呀!”约翰·莫尼埃说,“她们这么年轻美貌……她们为什么不到美国去,那里还会有别人爱她们……只要再忍耐几个星期……”
“到这里来的人,”她悲戚地说,“都是缺乏这份耐心……我们每个人在判断别人的事情时都很聪明的……不知是谁说过:人们总有足够的勇气来忍受别人的痛苦。”
这一天,坦纳托斯的旅客们都看到一对穿白色衣服的男女在公园里的小道上,在半山腰或山谷间蹓跶。他们热情地交谈着。夜色朦胧的时候,他们回到旅社,那个墨西哥园丁看到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便转过头去。
吃完晚饭以后,在一个单独隔开的小客厅里,约翰·莫尼埃一直在克拉拉·可贝·萧的身边窃窃私语,看上去她好象很受感动。后来,在回房间以前,他去找了包斯脱歇先生。包斯脱歇正坐在那里,前面放了一个很大的黑色帐本。他正在核算帐目。并不时地用红铅笔划掉一行。
“晚上好,莫尼埃先生!……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是的,包斯脱歇先生……至少我希望这样……我要对您说的事情一定会使您惊奇的……因为有这么一个很突然的变化……可是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啊!……总之,我是来告诉您,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不愿死了。”
包斯脱歇惊讶地抬起头来,说:
“您这是很认真的吗,莫尼埃先生?”
“当然!”那法国人说,“您一定会认为我变化无常,优柔寡断……可是,如果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那么改变主意不也是很自然的事吗?……八天前,我收到您信的时候,我正感到悲观失望,举目无亲……我觉得不值得再奋斗下去……今天,一切都改了样……而且归根结底,还得感谢您呢,包斯脱歇先生!”
“感谢我,莫尼埃先生?”
“因为创造奇迹的正是您介绍来和我同桌吃饭的那位夫人……可贝·萧太太是一位可爱的女人,包斯脱歇先生。”
“我早就对您这样说过,莫尼埃先生。”
“又可爱,又勇敢……她虽然已经知道了我的悲惨境遇,还愿意和我同患难……这使您惊奇吧!”
“一点也不……在这里,我们对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已经司空见惯了……而且,我十分高兴,莫尼埃先生……您还很年轻,很年轻……”
“所以,如果您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和可贝·萧太太明天就动身到地敏去。”
“那么,可贝·萧太太和您一样,也不再愿意……?”
“是的,当然是的……一会儿她还要亲自来告诉您的……现在还有一件事要解决……就是我付了三百元钱,这差不多是我所有的财富,是不是这笔钱得全部归坦纳托斯旅社?我能不能取回一部分,用来买我们的车票?”
“我们是正真的人,莫尼埃先生……我们没有为您服务到的,决不会要您付钱。明天早晨,会计室将给您结帐,除了膳宿每天二十元,再加上服务费用以外,余下的全部找回给您。”
“您非常客气,非常慷慨大方……啊!包斯脱歇先生,我该多感激您啊!我又找到了幸福……我又将开始新的生活……”
“为您效劳,”包斯脱歇先生说。
他看着约翰·莫尼埃出了门,走远了。于是,他便在一个电钮上按了一下,吩咐道:
“给我把萨各尼找来。”
几分钟之后,那守门人来了。
“您叫我吗,经理先生?”
“是的,萨各尼……今天晚上,就给113号房间放煤气……半夜两点钟左右。”
“经理先生,要不要先放催眠剂?”
“我想不必了……他一定会睡得很好的。……今晚就这一个,萨各尼……明天,就按照讲好的那样办,解决17号的两个女人。”
守门人出去时,可贝·萧太太出现在办公室的门口。

“进来,”包斯脱歇先生说,“我正想找人去叫你。你的顾客刚才来告诉我他将离开这里。”
“我值得赞扬一番吧……”她说。“事情干得不坏呀!”
“办得很快,……我会记住的。”
“那么就是今天夜里吗?”
“是今天夜里。”
“可怜的孩子!”她说,“他很温柔,很罗曼蒂克。”
“他们都是很罗曼蒂克的,”包斯脱歇先生说。
“你到底还是很残忍的,”她说,“正当他们对人生又感到乐趣的时候,你把他们消灭了。”
“残忍?……相反的,干我们这一行的人道行为就在这里,……这一位是信教的,有些顾虑,……我使他安心了。”
他翻开他的本子。
“明天,给你休息……可是,后天,我又有一个新客人交给你……也是一位银行家,可是这次是个瑞典人……并且不很年轻……”
“我倒挺喜欢这个法国人。”她茫然地说道。
“工作是不能挑的,”经理严厉地说,“拿去吧,这是你的十块钱,还加十块钱奖金。”
“谢谢,”克拉拉·可贝·萧太太说。
她把钱放进皮包,叹了一口气。
她出去后,包斯脱歇找出了他的红铅笔,很仔细地用一根金属小尺子,在他的本子上划去了一个名字。
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坛上,安德烈·莫洛亚非常特殊。至少在叙事风格方面,他是这一时代罕见的没有卷入现代主义流派的大师。他以传记文学和史学著作闻名于世,但其小说创作同样声名卓著,尤其是中短篇小说。
《坦纳托斯大旅社》是莫洛亚晚年的精心之作。如同任何一位古典主义大师一样,他有着设计故事的天才。处处碰壁的小人物约翰·莫尼埃在这样一个窄小的空间里活动并不显得如何局促,连同旅社的女雇员可贝·萧太太,甚至小说中只有寥寥数笔的旅社老板都生动可触、历历在目。从小说开始的简短对答,我们便进入作家创造的这一气氛中,我们随约翰·莫尼埃一起沮丧,绝望,同情他的不幸遭遇。故事的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牵动着我们的情绪。如果一掠而过,我们仅能得出小说是在讽刺人与人之间冷漠的金钱关系的印象。然而,只要我们略略用心,就可以感到这个坦纳托斯大旅社与卡夫卡的“城堡”一样是一种实在的象征,约翰·莫尼埃则因其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宿命结局而成为法兰西文学殿堂的又一个独特的典型。
就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特别是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莫洛亚面临着比其前辈更为困难的写作环境。在巴尔扎克、福楼拜时代,这一手法便已十分完备,各种典型形象几乎已经显尽了人类性格的各个侧面,十九世纪的文学巨人们已占尽了文学圣殿的整个空间,再想跻身其间,必须具备超人的天赋和努力。莫洛亚没有退缩。至少从《坦纳托斯大旅社》中所显示出的惊人造诣来看,他无愧于他的前辈。小说中简洁生动的对白,修裁得体的结构,以及精巧细腻的心理刻划都出自大家手笔。例如在到达坦纳托斯的描写中,就使人身临其境,一段段循序而下,都各具特色而不使人觉得繁复。那两位温柔多情的美貌女郎看似闲笔,但穿插小说前后却平添出一些色彩。再如小说的结局,委实出人意料之外,堪称神来之笔。萧太太所流露出的一丝温情,却使现实的残酷更加浓烈。特别是小说独特的轻松笔调,与人物命运的悲剧结局形成鲜明对照,使人扼腕而叹。
认为莫洛亚是个传统风格的作家,是在法国当代文学这个大的背景下相对而言。确实,在这篇小说中,他明晰流畅的思路,层层推进的手法以及干净利落的文字,都充分表现出传统风格的巨大魅力。然而,莫洛亚能在文坛独树一帜并且盛名不衰显然并非仅仅如此。因为,身处当代法国文坛,他必然地感受到现代主义意识的浸淫。约翰·莫尼埃这个小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独特的社会内涵,使我们不难发现他与萨特、加缪笔下人物的精神联系。因此,小说透出的“黑色幽默”的意味,对反理性的荒诞现实的讽喻也就顺理成章。
值得一提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气息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可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英国军队中担任翻译和联络官,并且因此创作出成名作《布朗伯尔上校的缄默》的原因。确实,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别出从斯威夫特到威尔斯、从斯特恩到赫胥黎的影响,英国文学中的理性主义色彩、审慎的有条不紊的思想以及严谨细致的文风似乎比法国传统文学中的浪漫精神对他的影响更大。而后者,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传记作品中。如果平心静气地阅读,仅就这篇小说而言,似乎也是如此。这进一步证明了一位伟大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世界的。
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