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还“红学”以学》看考证派是否误解了《红楼梦》
红学研究
不久前,笔者在网上发表《考证派是否误解了〈红楼梦〉》,在文中提出:“是不是胡适当初在进行《红楼梦考证》时,从根本上误解了《红楼梦》?是不是许许多多的学者们也跟着胡适‘走错了道路’,同样误解了《红楼梦》?”最近,笔者读到周汝昌先生一篇发表于10年前的《还“红学”以学》的大作,发现周老的大作为《考证派是否误解了〈红楼梦〉》一文,提供了更全面而有力的证据。周老在该文中指出,胡适先生当初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提倡他的白话文,且胡适对《红楼梦》几乎一无所知,更无半点好感,胡适的《考证》是在“空虚浮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此看来,考证派的开山祖师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从一开始就误解了《红楼梦》,便在情理之中了;许许多多的学者跟随着胡适“走错了道路”,同样误解了《红楼梦》,也就难以避免了。
正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从一开始就对《红楼梦》进行了误解,随之引起周汝昌先生为代表的众多考证派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的亦步亦趋。这些学者们为了维护胡适观点的正确,他们不但在胡适先生倡导的“大胆假设”的基础上越来越发扬光大,而且不惜以“造假作伪,恶语欺人”,“歪曲证据,以利己说”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继续对《红楼梦》进行自欺欺人的误解,从而造成了周汝昌先生在《还“红学”以学》一文中所形容的“红学的巨大悲剧性”,造成了考证派几十年来的考证观点和考证成果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越来越站不住脚的难堪局面。

胡适为提倡白话文而进行《红楼梦考证》,
造成《红楼梦考证》立论基础的“空虚浮泛”
周汝昌先生是中国当代考证派的主力和集大成者。1995年,周老应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龙协涛先生之约,发表了《还“红学”以学》的长篇力作,比较坦城地表达了他对“红学”前景的担忧。他认为,现在的红学界,缺少一些“敢与王、蔡、胡、鲁的学力识力相比”的学者参与,而是由一些“愧对先贤的今人来‘占领’此一学域”,从而形成了“一件十分可悲的文化现状”。
此外,在周老的这篇大作中,他老人家花了不少笔墨,披露出胡适当年进行《红楼梦考证》完全出于另有用心——“胡先生当时作考证,只是为了提倡‘白话文学’”;披露出胡适对《红楼梦》“这部书的真涵义真价值可说一无所论,简单肤浮得令人惊讶”。周老因此“深深诧异”:胡适“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钝而不明,若非亲历,实难置信”!
透过周老的《还“红学”以学》,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考证派的开山祖师胡适为什么一开始就误解了《红楼梦》的各种因素,还可以从几十年来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考证派为什么一直误解《红楼梦》得到多方面的解释和答案。
为了对周老披露的胡适当年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动机有进一步了解,对现在通称的“新红学”的先天不足有更全面认识,笔者将周老《还“红学”以学》第四部分“‘新红学’的不足之处”的相关论述摘录于下:
胡氏考证,在当时那种理解认识十分混乱的年代出现,确实贡献很大,说是具有科学性,不算夸张。但那毕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最初的事,回顾起来,当然不无遗憾之点。
第一, 先生晚年自述生平,对“建立新红学”很觉得意。但揆其实际,这只是一种“马后课”。胡先生当时作考证,只是为了提倡“白话文学”,选出几部小说名著,包括《镜花缘》《醒世姻缘传》,逐一为之“整理”,标榜“新式标点,分段排版”,然后给每部小说都作出一篇考证,冠于卷首,让“亚东”印行。他用力甚勤,多属开创工作,收获丰富,但他正是“一视同仁”,“平均对待”,初无任何特重《红楼》一书之意。这种考证,作者,年代,版本……,乃属于一般性的考据对象的共同内容项目。所以他从来也没有要建立一个“红学”专科学术的动机与观念。
他做了一般性的考订工作,贡献不小,但这儿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体系可言。
因此,从严而论,我们称之为“红学”,原是有些张皇其词了,胡先生自己也发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真曾建立了一种新的什么“学”。其实并非如此。
第二, ……
胡先生除了提出“自叙传”(相对于写别人而言是不错的),对曹雪芹这部书的真涵义真价值,可说一无所论,简单肤浮得令人惊讶——一个真正够得上“学”的专科学术体系,是不会那么空虚浮泛的。
也正因此故,他写了《考证》之后,只由于又得见《庚辰本》而作了一个“补考”而外,再也没有继续为“红学”作什么事情。即就搜求文献文物以及有关的各种形态的史料来说,以他的资望地位,以彼时的北京文化结构未经巨大动乱的有利条件下,他却放弃了努力征集的重要工作(义务、责任),除了收得《甲戌本》与《四松堂集》,就再也不见他关切此事了。
以上情况表明,他原无建“学”之意,当时关涉“白话小说”的任务一完成,就满足而止步了。
第三, 对曹雪芹的为人,对《红楼梦》的性质(特点、意旨、蕴涵……),他并未表现出什么探讨兴趣。不妨说,单层次历史考证而外所必需的思力、识力和更高层次的灵智方面的体会寻求,赏音参悟,一概欠缺。而用这种精神态度去对待这一主题,就使得“新红学”非常贫薄,够不止一种高级的文化学术的品位。索隐派人士的不服气,正是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 由于上一点原因,胡先生就连对“版本”的认识也是个模棱两可、自矛攻盾的“实践”者。
比如,他收得了价值极高的、可以代表雪芹真面貌精神的《甲戌本》,然而对这一珍贵文本却不见他发生多大的“整理”流布与深入研究的兴趣与愿望,《考证》写毕,即将此珍本束之高阁了。相反,他一直对那部程、高二次篡改歪曲原文最历害的《程乙本》大加欣赏,为之作序宣扬、排印流布,直至他晚年,仍然未见稍改早先的眼光与心情。
……
提倡在他的当时后世写文要白话,是可以的,但要用“白话化”来衡量中华历代的文学作品,拿它作为唯一的不可争议的标准,这就违反了历史和科学。——大量令人肉麻的庸俗拙劣的“白话”的得以流行与受赞美,皆由这个魔道而致成立。
……
我不禁深深诧异,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钝而不明,若非亲历,实难置信。
对以上这些,我起初只以为他是受了“意障”,即“白话障”,简单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所致。后来方逐渐明白:问题的根本是他的“西方意识”在指导一切。他是想把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特点特色都改成西方化——包括语言文字的民族精魂在内!因此,他不尊重雪芹原作的真实,而只是用程高篡本为他的“白话主义”服务而已。
……
就从一点来看,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于《红楼梦》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
可知世之所谓“新红学”,原是一种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周老倾其毕生精力于“红学”研究,自诩为“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1)以周老引以自豪的非凡的“智商”(2)和非凡的“学力识力”,特别是对“《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进行考证的执着,他老人家在其古稀之年披露胡适当年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动机,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贡献和失误予以评价,无疑是最具发言权的,他的这些发言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就如周老所言,胡适对《红楼梦》从来就没有好感。胡适曾自称:“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3)。他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4)正因为胡适对《红楼梦》并无好感,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以“西方意识指导一切”,“想把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特色都改成西方化——包括语言文字的民族精魂在内”的人,能对《红楼梦》的全部内容进行深透的理解;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对《红楼梦》并无好感的人,能对《红楼梦》中“故将真事隐去”的全部内容进行不可或缺的探究!再加之胡适当时既缺少时间也缺少兴趣对《红楼梦》进行深入研究,进行《红楼梦考证》的资料多是委托顾颉刚、俞平伯进行搜集整理,难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局限性。特别是他在发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时,又故意将自己已经推翻的一些明显错误的传闻当作证据塞进去,比如将已经自我否定过的袁枚《随园诗话》中“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数语,仍然当作了《考证》改定稿中的重要证据。胡适的这些很不科学的作法,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楼梦考证》的信口开河,甚至比周老所称的“空虚浮泛”还多了好几分虚假。周老说胡适的《考证》根本就“够不上一种高级别的文化品位”的评价,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周汝昌为谋取“受惠无穷”而进行《红楼梦新证》,
造成其《新证》离《红楼梦》研究的实质越来越远
经过周老《还“红学”以学》的介绍,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胡适当年进行《红楼梦考证》,“从来也没有要建立一个‘红学’专科学术的动机和观念”,人们对胡适的这一“红学”的评价,“原是有些张皇其词”了。那么,现在公认的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风行天下80多年,其间涌现出不少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大师,考证派至今掌控《红楼梦》研究话语权的现象又从何而来呢?纵观80多年的“新红学”发展历程,作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的周汝昌先生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要想比较全面地了解周老对“新红学”作出的“贡献”,还得从他老人家当年给胡适的信件中寻找其轨迹。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到,周老对“红学”的“贡献”,可以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那时,周老在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启发下,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5)发现了胡适先生久寻未获的《懋斋诗钞》,对此,胡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周老“《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6)
1947年12月,周老在《懋斋诗钞》基础上发表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7)胡适对周汝昌发表的这篇文章给予了鼓励。周汝昌因此而获得了接近胡适的机会,并且一步一步地得到胡适的“通体的指导”、“帮助”、“教正”(8)。为了感激胡适“那样恳挚指导”的“知己”之恩,(9)当胡适于《红楼梦》认识非常“简单肤浮”的情况下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后,周老“反视先生之后,并无一人继起作有系统的持续研究,为我派吐气,俞平伯先生的书另是一路,他完全没有在史实上下任何工夫,只是闲扯天,因此丝毫不能有所加于先生之说”,(10)便自告奋勇担当起为胡适先生“我派吐气”的重任。在胡适建立于“空虚浮泛”基础上的《红楼梦考证》引起众多学者质疑的非常时期,“先生(胡适)在这件(考证)小而又小的事上是孤立的”(11)关键时候,正好也是周汝昌直面“人微言轻的学生,在社会上想作任何理想的事亦困难万分”的窘境时,(12)“悟性”特好的周汝昌先生自然而然地“悟”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13),便主动向胡适提出“这个工作(周老现在称的建立在“空虚浮泛”基础上的《红楼梦考证》)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但尝试继承这工作。因为许多工作,都只开了头,以下便继起无人了,所以我要求创始的先生,加以指导与帮助。”(14)从而直接明了地求胡适先生“替我想一个”“真是受惠无穷的”“办法”,(15)让胡适先生为这位“人微言轻的学生”,找来尽可能可以找来的资料,让其进行《红楼梦》研究。
当时胡适大量事务缠身,还是为周汝昌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16)虽然胡适于1948年12月15日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匆匆飞离北京,周汝昌并没有放弃自己许给胡适“我既有此意,又已获得先生赞助,无论如何,决心力任此业”(17)的诺言。周汝昌先生以三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洋洋大观的《红楼梦新证》。之后,周老又撰写了《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曹雪芹小传》等系列著作,“悟”出了“脂砚即湘云”这一“平生在红学上,自觉最为得意而且最重要的一项考证(成果)”。(18)从而“构建了自己的红学体系”。(19)周老因此成为了新中国的“红学”第一人,成为了“考证派的主力和集大成者”。
然而,从周老与胡适往来信件所透露的信息中,我们除了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到周老为“新红学”作出“贡献”,还能了解到周老当年从事《红楼梦》研究,完全是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份“受惠无穷”的“理想的事(业)”。因此,我们就能看出为什么周老没有在几十年前及时向胡适指出《红楼梦考证》立论基础的“空虚浮泛”,而是在胡适建立于“空虚浮泛”《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了推波助澜的《红楼梦新证》;与胡适的《考证》相比,周汝昌的《新证》甚至更加偏离了《红楼梦》研究的实质,亦离周老《还“红学”以学》文中所谓“学”的范畴越来越远。尽管周老在《还“红学”以学》中,对胡适当年进行《考证》的动机并无任何褒奖之词,但这并不能掩盖他老人家当年纯粹是为了投身胡适的考证派的“为我派吐气”的门派之争,而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本来面目。如此说来,他老人家当初的动机是否纯正,所研究的方向是否正确,他的《新证》的研究成果有无客观公正的学术价值,能否经得起科学的论证和历史的验证,他为“新红学”作出的“贡献”有无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实在是值得人们玩味和怀疑的。
建立在周汝昌错误多多的《新证》基础上的考证派观点,
不可能对《红楼梦》做出科学的考证和正确的解读
如前文所述,周老的《还“红学”以学》花了不少笔墨,对胡适“为了提倡‘白话文学’”而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初衷进行了披露,但他老人家对自己的《红楼梦新证》究竟功过如何却避而不谈,对自己编写的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系列著作中相关证据是否经得起推敲和论证避而不谈,这也似乎说明周老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有失公允和客观。周老如今对胡适当年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动机给予了不无贬责的披露,但周老当年是出于结识胡适而进行《红楼梦》研究的,如他自己所说,“我如不因谈红楼,如何得与先生相识呢?”(20)而周老的《红楼梦新证》的观点,也是完全沿用了胡适《考证》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即论证“《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所以,即使周老的《新证》比胡适的《考证》资料更翔实,论据更充分,也不过是在胡适《考证》基础上的发挥和延伸,不过是为胡适的《考证》推波助澜和摇旗呐喊而已。
由于周老的《红楼梦新证》的资料翔实,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观点似乎有了更有力的证据支撑。特别难得的是,周老的这部著作于解放不久的1953年问世,在那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特定历史时期,周老的《红楼梦新证》正好填补了国内相关学术领域的空白,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学术领域带来新的话题和活力,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远远超过了他撰写该书的初衷。周老的《红楼梦新证》,终于为他自己开创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受惠无穷”的“理想的事(业)”。(21)
周老的个人愿望是很快就实现了,令人遗憾的是,他老人家的《新证》是从胡适“空虚浮泛”的《考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周汝昌先生穷其毕生精力,对胡适先生最先确定的“《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这一命题进行考证,在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进行全面考证的基础上创立出自称的“芹学”(22)。就因为胡适《考证》基础的“空虚浮泛”,所以,周老及众多的考证大师们按胡适的《考证》思路考证了几十年之后,至今也搞不清胡适所要“考证”的《红楼梦》著者曹雪芹到底是何方神仙,搞不清这个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儿子还是曹寅的孙子。从这个层面来说,无论是胡适的《考证》,还是周汝昌的《新证》,都成了“空虚浮泛”的学说,都成了“将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
随着对《红楼梦》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但有学者和周汝昌先生一样,对胡适当年的《考证》进行点评和反省,也有学者对周老的《新证》进行重新的研究和论证,并发现周老的《新证》谬误多多。如王利器先生就专门写出《〈红楼梦新证〉证误》一文,尖锐地指出《红楼梦新证》存在“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贩、顾此失彼、道听涂说、数典忘祖、前知五百年”十类硬伤。(23)王利器后来又指出,“《红楼梦新证》,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在他(周汝昌,下同,笔者注)的书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这是怎么搞出来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类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既然周老的《红楼梦新证》也存在如此多的错误,周老为其忙了一辈子的曹雪芹之说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越来越站不住脚,由此看来,周老的学术生涯学术体系不仅存在巨大漏洞,而且也给红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悲剧”。因为从中国新红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现在通称的主流“红学”即考证派的主要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胡适的《考证》和周老的《新证》的基础上的。就连现在通行的曹雪芹死于1763年(壬午)除夕的说法,几十年来进行的曹雪芹逝世多少周年的纪念活动,也是在胡适《考证》、周汝昌《新证》的基础上确定的。刘梦溪先生对此评价说: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只是给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才真正构筑了一所较为齐全的住室。”(24)
孙玉明先生亦认为:
《红楼梦新证》是周汝昌的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红学专著。这部“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以其开创意义和资料的丰富详备,在红学界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
一般认为胡适是“新红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在俞平伯和顾颉刚的帮助下,他只是完成了“新红学”开山立派的初期工作。周汝昌则是“新红学”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新证》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所有问题,堪称该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25)
若是以周老的《还“红学”以学》的相关论述为标准,并以周老审视胡适当年进行《红楼梦考证》的眼光,来审视周老的《红楼梦新证》,很多学者都知道周老的《新证》不过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份“受惠无穷”的事业,按胡适的《考证》的基本思路,用图书馆的资料拼凑而成的。周老的这部《新证》在解放初期虽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并不能说明一个毫无社会阅历可言的大学生,能编著出一部无懈可击的学术专著来。周老在《还“红学”以学》中称:“百年过去了,如今这一辈的人,又有几个敢与王、蔡、胡、鲁的学力识力相比?由这些愧对前贤的今人来‘占领’此一学域,我则感到是一件十分可悲的文化现状。”同样的道理,当时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周汝昌,又岂能与王、蔡、胡、鲁的“学力识力”相提并论?他所进行《红楼梦》研究的出发点,又怎能和王、蔡、胡、鲁的出发点一视同仁?如果周老具有王、蔡、胡、鲁的“学力”,其《新证》又怎会被王利器先生证出“几乎每页都有错?”如果周老具有王、蔡、胡、鲁的“识力”,又怎能对王利器先生多年前提出的错误一直置之不理?
老至今还自称,“我自知并没有充当红学家的真实的德才学识。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不自揣量,那真是不知愧耻之尤了。”(26)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周老甚至称自己“是个大俗人,大陋才,大卑识,大禄蠹”。(27)如果仅仅以周老的《新证》和相关著作,来确定连自己都没有任何底气和自尊的周汝昌先生是考证派的集大成者,就如周老对胡适的《考证》的评价,“原是有点张皇其词”了。如果指望以胡适 “空虚浮泛”的《考证》,以周汝昌“几乎每页都有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红学”,能对《红楼梦》作出科学的考证和正确的解读,无疑是寄望过高了!
周汝昌对考证派的自揭家丑,
再次揭示考证派面临“眼前无路想回头”的必然选择
周老或许意识到自己的“自传说”观点越来越破绽百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便在《还“红学”以学》中,搬出“鲁迅大师”一些并不全面的相关论述给自己壮胆,把鲁迅先生说成“也是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列出的证据之一就是鲁迅先生“在杂文中他也风趣地写出了这样的话: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曹雪芹整个儿地进了小说。”
然而,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如他对《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8)的说法是全面而公正的,根本不存在周老所言的鲁迅先生“也是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周老对鲁迅先生的只言片语进行了片面的吹捧后,笔锋一转,又以一种欲言又止的语气抖出了红学界10年前的种种弊端。并语重心长地指出《红楼梦》研究中“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社会群议对‘红学界’的印象并不是十分良好的,而最其根本的症状就是号称红‘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
从本文观点的角度看来,周老“临文不讳”所披露的种种现象,也是造成考证派多年来一直误解《红楼梦》的主要原因所在。既然周老从另一个侧面论证和补充了这一本文想要表达的主题,且以周老特殊的身份提供了堪称权威的相关素材,笔者再将周老《还“红学”以学》“艰难的推进”中的一些自称“不无顾虑的”论述摘录于下:
(一)充分的迹象表明:毛泽东主席自1953年秋为始,忽然显示出对《红楼梦》的兴趣与重视,在此后数年间多次谈话中都传出了他讲论“红学”的看法。海内外都认为这是建国后“红学”较之前代更为兴盛的一个原因。
(二)与此同时,1954年发起的批俞(发展成为批胡……)运动又给红学研究带来了另一种影响。由于执行奉行者的偏差,学术变成了为某一时期政治需要的口号机械服务的工具。上面传来的一句话,往往即成为“红学论文”的下一个主题。这样的结果是大量的评红论红文章皆由一个既定概念出发而去寻觅“论据”,片面强调某一论点,而并不是从《红楼梦》的客观本体及其特性特点中作具体研析而得到的结论。
在此情势下,“红学”之“学”的质素成分,当然就越来越微了。
(三)再进一步,就衍变而出现了“阶级斗争红学”。这种论点的书,以化名“洪广思”(冯其庸先生的笔名,笔者注)的《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为之代表。这当然就离开学术更远了,今不必多加评论。至于此类的“影射红学”“儒法斗争红学”等等相继演出,于是“红学”扫地尽矣。
当政治局面影响学术达到如此地步之时期,想做真实学问的处境是困难万分的,这不待多说自明。但也还有另外的学风问题,加重了这种困境。今亦试举其具有代表性影响的如下——
…… ……
3.造假作伪,恶语欺人。
这一类略分三种:一是假编“传说”,凡传说者必有一定普遍性即有一方一族之人皆大略知之,世代递述;而假传说则只有其?艘桓觯薰蚕掖呷缤八凳椤保耷畹摹跋附凇保缢砬啄慷谩6俏痹煳淖质妨希缡裁础凹濉薄凹褪ⅰ钡鹊龋笾掠搿按怠庇泄餐恪安宦撞焕唷保淖衷蛴任拷牛ㄒ煌芍癯跏逼谥佟拔难浴保H俏痹臁拔奈铩保分植灰唬哉偶彝濉盎蔽浯恚ㄒ延兄槿嗽凇妒咏恰吩又旧辖椅保?
以上三者,谬种流传,一般文化水平不足者为其所欺,辗转引录,流毒极广。然而此种作伪大抵怕人揭露,凡表疑问者即以下流恶语伤之,态度恶劣。
4.学风与学德。
这儿用“学”字已是十分勉强了,因为我不拟涉及“学”以外的不忍言之事,姑且用之以示范围。
一种学风是自己逞臆妄说,而不许人异议,凡表不同意者,即设词辱詈,群众至谓之为“骂街红学”。一种是巧妙稗贩他人学识,而专门以“反戈一击”为手段,以图贬人扬己,此种例不胜举。
一种是“霸势”,企图垄断一切,“人莫予毒”。
一种是以“手法”代治学。至于不惜歪曲证据,以利己说。……
作为“红学”权威机构之外的局外人,笔者固然不便对周老披露的“红学”机构中的种种不堪现象妄加评论;也不想在本文中对已经过时的“阶级斗争红学”、“儒法斗争红学”进行深入探讨;更不必对周老披露的红学界“造假作伪,恶语欺人”等种种“企图垄断一切”的“霸势”,“不惜歪曲证据,以利己说”的现状予以点评。时过境迁,也许周老十年前谈及的红学界某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陋习早已荡然无存,或许有了很大改观。但是,一些红学权威至今不能接受不同学术观点的情况还是不同程度存在。他们仍以不同方式,对《红楼梦》的作者和主题进行误读和误解,仍对不同观点的学者和学术文章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压,甚至对一个同样缺乏证据而开创“秦学”的刘心武先生群起而攻之。他们自己却仍然抱着一个子虚乌有的曹雪芹大唱赞歌。就考证派现在的出发点而言,或许早已经不是对《红楼梦》进行科学的纯学术的研究了。如果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为了提倡‘白话文学’”,周汝昌的《新证》是为了给自己谋一份“受惠无穷”的“理想的事(业)”,那么,现在的考证派大师也无非是在《红楼梦》已经完成了为阶级斗争服务,为儒法斗争服务的历史使命后,让其继续为自己谋求一项“受惠无穷”乃至“受惠”终身的事业,谋求一项永远冠冕堂皇的“红学大师”的招牌;让其继续维持自己本已摇摇欲坠的“红学权威”的合法地位。为了维持这个极具诱惑力的地位,为了维持考证派继续垄断继续误解《红楼梦》的合法性,当今红学界的代表人物冯其庸先生表示 ,还要对《红楼梦》研究一千年(29)!甚至有学者还在高呼“曹雪芹万岁”!(30)
为了对《红楼梦》的考证持续一千年,为了让这个曹雪芹活到一万岁,为了使一个查无实据的曹雪芹给一代又一代的考证派大师提供“受惠无穷”的“理想的事(业)”,直到去年,仍有红学界的权威人士(包括周汝昌先生)联署向北京市有关部门呼吁,要求再建造更大规模的“国家级曹雪芹纪念馆”(31)。只是他们的这一要求,再也不象四十年前(1963年)那样,能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是被北京市有关单位以其“证据不足”拒绝采纳。对此,周汝昌先生也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因为实在“拿不出真证据”而“爱莫能助”了(32)。这说明,现在的相关权威机构也认识到了考证派关于曹雪芹之说的“证据不足”,认识到了某些考证派大师的自欺欺人。
概而言之,一部归根到底不过是小说而已的《红楼梦》,也是当时民间的读书人以“一把辛酸泪”“敷演”出来供世人“消愁破闷”的“假语村言”。这样一部来自民间的小说,根本不值得一代又一代的“红学大师”穷其毕生精力,在《红楼梦》“满纸荒唐言”的基础上,为一个书中虚拟的作者名字,进行没完没了的“荒唐”的生平家世考证;更不值得两百多年后“红学大师”一面刻意抹杀书中“故将真事隐去”的反清思想,一面肆意为自己站不脚的考证观点“造假作伪”,“伪造文字史料”。对为胡适《考证》辛苦了80多年的考证派而言,余英时先生早在1976年指出,“红学考证基本上已尽了它的历史任务”。(33)俞平伯先生早在80年代初提出“除了再有新资料发现,(考证派)能做的事已经很少” 。(34)并于1985年作出了“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了”(35)的总结。看来,考证派的大师们在经历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的辉煌之后,不得不面对余英时先生近三十年前一语破的的“眼前无路想回头”的现实,不得不面对周老自揭家丑的难堪,或者“功成身退”,或者改弦易辙。而要真正实现《红楼梦》开头提出来的“谁解其中味”,恐怕还得民间一些不以“受惠无穷”为目标,却以“同消寂寞”“陶情适性”为乐趣的“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闲人”们来参与。
注解:
(1)、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扉页
(2)、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 第9页
(3)、《胡适红楼梦研究论文全编》 289页
(4)、《胡适红楼梦研究论文全编》 290页
(5)、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 149页
(6)、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胡适致周汝昌函 306页
(7)、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104页
(8)、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函 319页
(9)、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函 319页
(10)、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函 320页(其中“他完全没有在史实上下任何工夫,只是闲扯天”在《胡适红学年谱》中被删,此数语来自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因为该书中有“周先生特别申明:‘未经我本人同意,不得随意转载。’”此处引文未经周老同意转载,特向周老致谦。)
(11)、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函 320页
(12)、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函 321页
(13)、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函 316页
(14)、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函 310页
(15)、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函 321页
(16)、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胡适致周汝昌函 302页
(17)、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函 313页
(18)、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 184页
(19)、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105页
(20)、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函 314页
(21)、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周汝昌致胡适信 321页
(22)、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曹雪芹.后记》 245页
(23)、《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辑 403页
(24)、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104页
(25)、孙玉明《红学:1954》 287页
(26)、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 351页
(27)、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 351页
(28)、鲁迅《红楼梦》杂记 《鲁迅全集》第八卷
(29)、2005年6月3日至5日,冯其庸先生在由河南教育学院和中国红楼梦学会共同主办的“百年红学的回顾与反思——2005年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上说:“红学研究是没有尽头的,我曾说可以再研究一千年,这个一千年只是个概念,红学是无穷无尽的,有开头,什么时候结尾谁也不能说;非但没有尽头,还在不断地发展。”
(30)、傅光明主编《新解红楼梦》286页,傅光明:……最后用胡(德平)先生书中的一句话作为结语吧:曹雪芹万岁,《红楼梦》无疆!
(31)、《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3期第1页
(32)、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345页
(33)、《海外红学论集》余英时《眼前无路想回头》 113页
(34)、《我读红楼梦》第37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
(35)、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 530页
2005年11月21日于深圳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
红楼梦曲:引子、枉凝眉、终身误、恨无常、喜冤家、分骨肉、虚花悟、乐中悲、世难容、聪明累、留余庆、晚韶华、好事终、飞鸟各投林
金陵十二钗副册:甄英莲(香菱判词)、平儿、薛宝琴、尤三姐、尤二姐、尤氏、邢岫烟、李纹、李绮、喜鸾、四姐儿、傅秋芳
金陵十二钗又副册:晴雯(判词)、袭人(判词)、鸳鸯、小红、金钏、紫鹃、莺儿、麝月、司棋、玉钏、茜雪、柳五儿
十二贾氏:贾敬、贾赦、贾政、贾宝玉、贾琏、贾珍、贾环、贾蓉、贾兰、贾芸、贾蔷、贾芹
十二官:琪官、芳官、藕官、蕊官、药官、玉官、宝官、龄官、茄官、艾官、豆官、葵官
十二家人:赖大、焦大、王善保、周瑞、林之孝、乌进孝、包勇、吴贵、吴新登、邓好时、王柱儿、余信
其他人物:贾母、王夫人、薛姨妈、赵姨娘、邢夫人、林如海、贾雨村、甄士隐、刘姥姥、柳湘莲、薛蟠、贾瑞...了解更多人物,及诗词关注公众号(bcbeicha)杯茶读书,回复关键字获取。
红楼诗词:西江月二首、葬花吟、题帕三绝、五美吟、秋窗风雨夕、柳絮词、菊花诗、桃花行、芙蓉女儿诔、姽婳词、怀古绝句、
红楼梦每回主要内容及解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一零四、一零五、一零六、一零七、一零八、一零九、一一零、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七、一一八、一一九、一二零、
重要情节:黛玉入府、梦游太虚、元妃省亲、宝玉挨打、宝钗扑蝶、共读西厢、黛玉焚稿、湘云醉眠、可卿之死、紫鹃试玉、探春理家、惑馋抄园、
脂批红楼梦每回原文解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
微信搜索公众号【杯茶读书(bcbeicha)】关注后,在对话框发送人名,获取相应的人物分析,如:黛玉。回复诗句,获取相关诗句解析,如:葬花吟。回复回目,获取相应回目的简介及分析,如:红楼梦第一回。其他更多的回复关键词等你探索,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简爱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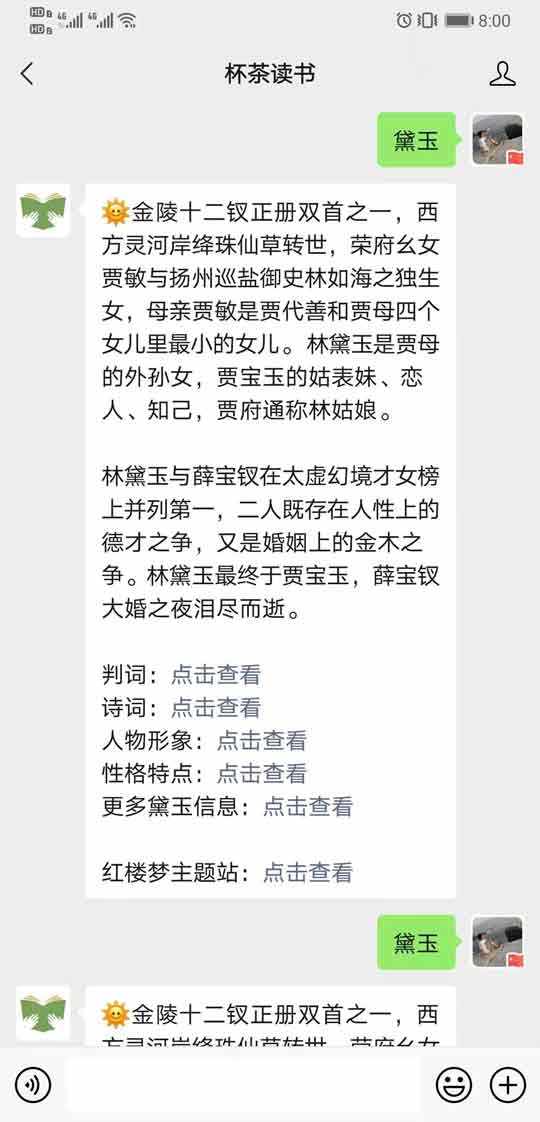
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