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有二伯的人物形象
一、单纯与狡黠,善良与贪婪中的性格矛盾
六十岁的有二伯被三十多岁的父亲,打倒了,孤零零的躺在地上,夜里的时候,老厨子嚷着,有二爷上吊了,然而,并没有。“等我再拿灯笼向他脸上一照,我看他用哭红了的小眼睛瞪了我一下。”过了段时间,有二伯又跳井了。“开初一动不动,等人都来全了,他开始往井边上跑”有二伯还是活着。这些愚顽和颇滑稽可笑的行为,使“老厨子说他贪生怕死,别人也都说他死不了”[1]。有二爷怕死吗,他给“我”讲毛子来的时候,很胆大,“不知怎么的,他一和祖父提起毛子来,他就胆小了,他自己越说越怕”,有二伯自然是不怕的,但是前后相反的言行,并没有过多的恶意和坏的影响,这个愚顽的可笑近于可爱的老头,只是希望人们或者说张家的人记得他曾为张家做过的事情,不要将他视为“家族以外的人”。

老厨子问有二伯喝酒是用铜酒壶好还是锡酒壶好,“用各种的话戏弄着有二伯”,有二伯认真的,一本正经地回答,以至于被老厨师套出了话,“哪有那么贵的价钱,好大一个铜酒壶还卖不上三十吊呢”以及拿有二伯偷卖澡盆的事由,嘲弄他。于是俩人不免打骂起来,尤其老厨子骂有二伯是个老“绝后”,真真的触痛了有二伯的心,自己哭悼自己。而后“他们两个又和和平平地,笑笑嘻嘻地照旧地过着和平的日子”。有二伯并不记仇,相反单纯近于愚。有二伯带着“我”去公园的时候,总是急急地催赶着,以免花钱,因为“你二伯没有钱”。此刻他是窘迫的,但也只能无可奈何的劝慰我“回家罢!”,他在贫瘠破落中也只能给予“我”一点言语上的安慰有二伯和冯歪嘴子谈话,从来没有偷着溜过,彼此说完了话,还会客气一番。而不像老厨子常常蹑手蹑脚的就溜了,让冯歪嘴子空说一大段。
总之,有二伯是一个认真、单纯、善良的,有着孔乙己的影子(好面子)和阿Q的印迹(滑稽)的老头,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真实而又生动。
二、喜剧性语言下的悲剧性人物
从《呼兰河传》到《家族以外的人》,萧红的小说、散文常采用儿童化视角,这也导致作家在作品中对待人事的批判,没有明显的表现,而近于客观化的描述。但作为研究者,就应以犀利的眼光,真实的语言揭开作家为作品披上的温情的面纱。作家以轻喜剧的语言描述的实则是一个悲剧性的世态,尤其在这世态中生活的典型——有二伯。
有二伯偷澡盆一节,夏日的午后,大家都睡了,一切静悄悄的,“就在这样的一个白天,一个大澡盆被一个人掮着在后花园里边走起来了。”那澡盆很深,从有二伯头上扣下来,一直扣到他腰间。行走的样子滑稽可笑。因此,常常家里丢了东西,暂时找不到的东西,甚至是老厨子偷拿走的,也都算到了有二伯的头上。这样的结果,自然是使父母亲更加厌烦起有二伯。用一个词“为老不尊”来形容,并不过分。况且父亲是一个“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有二伯的身份地位是尴尬的,他不是张家的人,“三十多岁来到我家”,然而他的半生又在“我”家度过,又似乎是家里人的一份子。同样在另一篇文章《家族以外的人》中,关于有二伯的描写只提到一句:“有二伯回来了”。夜幕早已来临,却没人关心,只有狗吠和贪玩的孩子,明显的,有二伯就是题名所指的“家族以外的人”。他就是这样生活在一种尴尬的处境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地主家长工的角色虽不是重点表现对象,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长工的作用很大,他是一个廉价的长期劳动力,有时候甚至充当大管家的作用,有着忠奴义仆的意味,且与东家的关系极好。如《白鹿原》中白家的长工鹿三,东家白嘉轩喊他三哥,让自己唯一的女儿认鹿三当干爹,给鹿三的孩子黑娃交学费,给兔娃娶亲等等,而鹿三也为白嘉轩做出了许多忠义之举,为了身为族长的白嘉轩维护好白鹿原上的风化,残忍杀死了自己的儿媳田小娥,其中有其愚昧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为其东家着想。而有二伯并不是如鹿三一样的长工,尽管他如鹿三一样为东家尽心尽力,但鹿三有自己的家庭,有妻有子,而有二伯如老厨子所言是个老“绝后”,连个安身的住所都没有,飘飘荡荡,到了年老体弱,也会遭父亲打,遭母亲谩骂,遭老厨子嘲弄。有二伯的结果,有咎由自取之处,更多的是身不由己的无奈。
三、悲剧人物预示下的悲剧世态
有二伯在张家理应受到不一样的对待,这些也是有二伯生活在张家的资本。然而现在的东家不是祖父,现在也不是“二东家”的时代了。这一角色正如《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只出现了一次,即第七回中一片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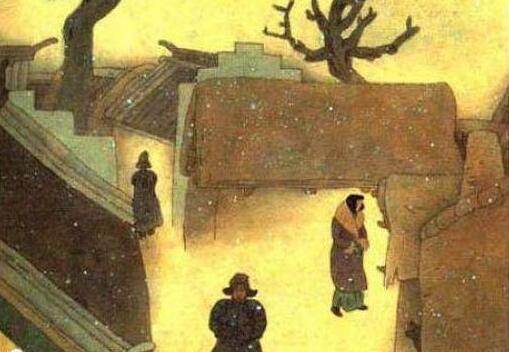
焦大从小跟宁国公贾演出过三四回兵,曾从死人堆里把奄奄一息的主子背出来。这样的功劳使贾家的长辈优待贾大。然而时过境迁,到了贾琏这一代,从主子到其他众家仆,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次,外头打发焦大送秦相公,没想焦大醉了酒因趁着酒兴很明显焦大借酒兴骂出心中的不快,不仅是抱怨给他安排的差事不公,更多的是一种揭露。正如鲁迅先生说,“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恐怕也會有一篇《离骚》之类。”[3](p712)由此,焦大的借酒谩骂,貌似在“倚老卖老”中,确认其身份地位。其实首先是出于对分配差事不公的发泄,也有对贾家忘恩负义的指责然而在他的骂斥中凸显的更多的是实质性的问题:贾府家势趋微,破败指日可待。如同有二伯,在近似疯癫的无礼的谩骂与指责中,以及在悲哀的自语与自白中对张家家道的衰退,所感到的无奈和悲哀。自己的悲剧命运就成为世道衰退,社会落后的象征。
尽管有二伯是这个不公社会牺牲者中的代表,他自身又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然而如前所述,在萧红看来,同情和关怀是首先的,在《呼兰河传》尾声中,作家还以充满感伤的笔调写道:“听说有二伯死了,就是老厨子活着年纪也不小了”。此外对于有二伯她还有这样的情感“有二伯虽然做弄成一个耍猴不像耍猴的,讨饭不像讨饭的,可是他一走起路来,却是端庄,沉静,两个脚跟非常有力,打的地面冬冬地响,而且是慢吞吞地前进,好像是一位大将军似的。”这是一种仰视,敬爱。萧红如同有二伯无力去改变自己悲剧的命运一样而无法阻止这个衰退的世界。有二伯的悲剧就是世态的悲剧。
参考文献
[1]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M].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2]萧红.萧红作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3]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刘玉梅,女,聊城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老舍研究。
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