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①、苏子由②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
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扬子③《太玄》、《法言》,昌黎④甚好之,故昌黎文奇。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
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
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
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自是未备。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至先秦战国,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⑤集其大成。唐人宗汉,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纵,而失其厚茂,气味亦少薄矣。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何可节损?然枝蔓软弱,少古人厚重之气,自是后人文渐薄处。史迁句法似赘拙,而实古厚可爱。

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
译文:
写文章的方法,以精神为主,以气韵补充。曹丕、苏辙品评文章,以气韵为主,正是这样的。但是气韵随着精神变换,精神浑厚则气韵充盈,精神悠远则气韵飘逸,精神雄伟则气韵高洁,精神变幻则气韵奇异,精神深沉则气韵平静,所以精神是气韵的主导。至于写专门的论文以讲道理为主,则不能全部展现文章的奥妙。如果人不熟读经书洞彻道理,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就浅陋空荡。人如果没有组织文字的才能,则文字纵然再多,都不适用。所以道理、书籍、组织文字的能力,是写文章的要素。
文以奇为贵,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最珍贵最喜爱的东西,必定不是平平常常的物件”之意。然而,有的文章奇在字句上,有的奇在内容上,有的奇在行文上,有的奇在构思上,有的奇在深远的意境上。有的奇在气韵,有的奇在精神。仅仅是字句奇,不足以称奇,气韵奇特才是真的奇特;精神奇特是自古以来很少见到的。各种所谓奇特的等次地位虽然是这样的,但字句也不可平淡无奇。扬雄的《太玄》、《法言》,韩愈非常喜欢它,所以韩愈的文章就很奇特。文章的奇特的气韵是最难认识和掌握的,大体说来,就是要忽起忽落,气之来也没有端绪,气之去也没有痕迹。读古人的文章,在起落转接的地方,觉得有难以探测、不可捉摸之处,便是奇特的气韵。
文章贵在简洁。凡是文章,笔法老练就可以简洁,感情真挚则可以简洁,言辞确切则可以简洁,事理精当则可以简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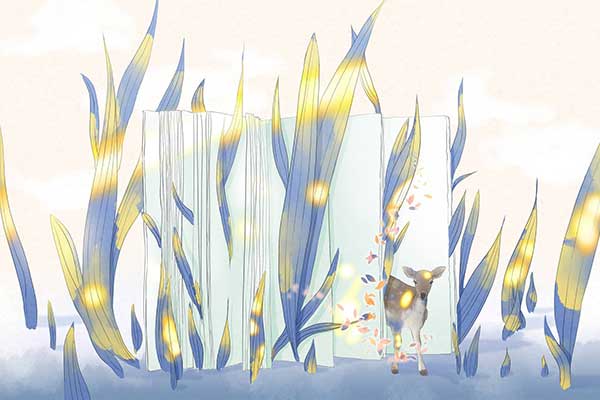
文章贵在讲究变化。《易》中说:“老虎随季节而换毛则毛色更加光亮,豹子随季节而换毛则毛色更加鲜丽。”又说:“事物相互交杂,所以才称之为文章。”因此所谓文者,说的就是变啊。一本集子中的文章篇篇变,一篇文章中的章节段段变,一段文字中的语言句句变,精神在变,气韵在变,境界在变,音节在变,字句在变,这只有韩愈能做得到。
行文的方法有平实有奇特,应该是兼而有之,才能充分显示写文章的本领。上古时代,文字刚产生,实字多,虚字少。《尚书》的《典》、《谟》《训》、《诰》,文字十分简朴古奥,这样是(由于)当时的文法还不完备。到孔子的时候,虚字已经详细而完备,于是写文章的人就能够将所要表达的事物的神气形态全部描绘出来。《左传》的情致和韵味都很美,文章光彩耀眼。到了先秦战国时代,就更加疏荡恣肆。汉朝人有所收敛,稍微走向了刚劲质朴,只有司马迁能集其大成。唐朝人宗法汉人,然多数趋于峭拔硬挺。宋朝人宗法先秦,得到了先秦文章疏荡恣肆的一面,但却有失于浑厚丰赡,情气韵味也显得有些淡薄。写文章必须虚字用得充分而后方能使精神情态全部显现出来,怎么可以随便节制减损呢?然而枝蔓敷展软弱无力,缺少古人那种浑厚沉郁的情气,就是后人的文章越来越浅薄的地方。司马迁文章的句法看起来似乎累赘重拙,而实际上那正是它古朴厚重可爱之处。
道理不能够直接表达,因此文人依据事实阐明道理;感情不能够直白地表达,因此文人凭借外物寄托情感。依据事实阐明道理,是《庄子》的文法;凭借外物寄托情感,是《史记》的文法。
注:①曹子桓,曹丕;②苏子由,苏辙;③扬子,西汉文学家扬雄;④昌黎,韩愈;⑤子长,司马迁,下文史迁也指司马迁。
相关推荐



